一
一切将逝去,如苹果花丛的薄雾。
——叶赛宁
张爱玲在她的自传小说《小团圆》的开头劈面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在那水气泱泱的文字里,她的情意,宛如丝绵蘸胭脂,是洇得一塌糊涂的嫣然百媚。
总有人替她不值,甚至《小团圆》的初稿完成之后,她给宋淇看,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然而宋淇却写了六页纸的信力阻《小团圆》的发表。宋淇的理由很充分,当然更现实,无非是说:“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除此之外,宋淇还顾虑胡兰成会借此大出风头:“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那年,胡兰成正在台湾文化大学任教,著书立说有一定
影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郑愁予、痖弦、蒋勋、张晓风都曾听过他授课。但由于“汉奸”身份,本地文坛对他一片挞伐。当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山河岁月》。彼时,台湾是张爱玲唯一的中文出版市场。作为胡兰成前妻,张爱玲身份敏感,难免牵扯不清。
然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却得以再版,那本书的扉页上印着:“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宋淇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也未必全然正确,张爱玲向来是“愈寒衣逾薄,未肯惜腰身”,何曾将“政治”萦挂于心?她一生最怕听交响乐,只因“交响乐宛如政治一般,急管繁弦,各种巨响浩浩荡荡地冲来,让人无力抗拒”。只是这一回,张爱玲却有见解随众、应酬世情的俗骨。
更何况,以胡兰成的才华,又何曾需要“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胡兰成逃亡至日本,在1951年发表的《毛泽东论》,他写道:“我住在日本,时常突然会感到非常寂寞,彼时会立即想起毛泽东,也还只有他在我身边,他在此后不断变化,渐渐从我的脑海中远离,然而我亦只像唐诗‘西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所描绘的境遇来理解他。”
胡兰成还说:“毛待人接物时的态度极其自然,部下与他在一起毫无拘束之感。此外,他飞扬的态度,就像君临奥林匹斯山的神,俯视着遥远的众人。使人感受到他无所不知的英雄气概与哲人的气息。而他又非常具有人情味,无论怎样无聊的人都会与之一起谈话,看戏剧,吃糖果糕点,并递茶邀烟草,其中完全没有造作,显得十分融洽。”
胡兰成还谈叛逆之美,举例说:明人的诗中有“双眉画不成,十五背娘行,独自摇兰桨,横塘看月升”,他将这诗词来比拟一代新人的开国精神。
这神来之笔,纵览民国,只有张爱玲才是与他最登对的那个人。张爱玲看胡兰成在房里,她写下:“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那简短的文字声色俱备,有着含蓄却又呼之欲出的情意,那是一个女子对心爱男人的倾慕,更有一名写作者对另一名写作者的相知与相惜。
身材高大的张爱玲在胡兰成一时找不到好句子来形容她行坐走路时,忍不住指点他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动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淹然二字就用得好。”她又进一步解释“淹然”二字:“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还没有任何一种感觉或者意态形致,是张爱玲所不能描写的。
胡兰成初见张爱玲,回来忍不住写了一封短笺给她:
爱玲先生雅鉴:
登高自卑,行远自迩。
昨日自你处归来,心头盘唱这八字。
上海的云影天光,世间无限风华,都自你窗外流过。
粉白四壁,乃是无一字的藏经阁,十八般武艺,亦不敌你素手纤纤。
而张爱玲则赠了一张照片给他,在照片的背面,她用谦卑至极的语气写道: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那一问,这一答,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彼此呼应;亦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美好的时光就像女孩儿初学刺绣时绣下的花骨朵儿,娇艳饱满。
香港作家亦舒曾评说过这段情事:“胡兰成以张爱玲做标榜,写《今生今世》,口口声声:‘爱玲,爱玲’,却在做夫妻的时候,招蜂引蝶处处留情,甚至公然带姘头给她看,做妻子的有什么幸福可言?为人丈夫的又有什么可称道?一纸婚书,终是成了笑柄。”
亦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想来是忘了自己年少时经历的那些事:她17岁倒追画家蔡浩泉,违抗父母阻拦闪婚,生下儿子,并在儿子一岁时离婚。43年过去,她的儿子蔡边村在德国柏林影展上播出纪录片《母亲节》,片中蔡边村作为导演亲自出镜,想要寻找妈妈,那年他44岁。他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在11岁时,母亲带他进电影院看《007》,买了一只机器人玩具,此后再无音讯,多年来,他寄出的信从未得到亦舒的回复。亦舒的哥哥倪匡也说20多年没有与亦舒通过一次电话。与蔡浩泉婚姻失败后,亦舒狂恋上男明星邱岳华并与之同居最终分手。几次失败的恋爱后,她转身成为香港最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里,女主角都是狠角色。
亦舒倒真有与张爱玲一脉相承之处:个性骄傲,绯闻缠身时任由流言肆起从不回应,一样凉薄与彪悍。只是她却忘了男女情事向来不足为外人道也。
倒是木心说的话更合乎人性:“爱情显得好时,不是爱情,是智慧和道德。”“不必让肉体升华。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即便是如张爱玲与胡兰成那般才华横溢,也终是逃脱不了复杂人性的走向,就像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一样,他们的世界终是要走向幻灭。
二
我遇见你,我记得你,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
——杜拉斯
上海名作家程乃珊母亲与张爱玲曾是同学,就读上海圣约翰贵族名校,她母亲说:“张爱玲并不起眼,不和人来往,不说话,又瘦又高,人缘不好,很多人排斥她,总是独来独往。”“张爱玲成名了,亦不和人来往,一生的朋友,只有一个叫炎樱的黑胖女孩子,两个人是看一眼就天地洞开的那种,就连她的婚姻,也只有炎樱在场。”
这段回忆可信度非常高。1936年夏,在高中二年级班级合影中,张爱玲立于后排,身著暗色旗袍,体形单薄,落落寡合。1937年的高中毕业照中,很多女同学烫了新潮卷发,穿得花团锦簇,张爱玲依然立于后排,仍是一袭式样陈旧的深色旗袍,神情萧索。
多年以后,张爱玲自己在《小团圆》里也是这般描述自己:
“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卷的长发。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么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九莉戴着淡黄边眼镜,鲜荔枝一样半透明的清水脸,只搽着桃红唇膏,半卷的头发蛛丝一样细而不黑,无力地堆在肩上,穿着件喇叭袖孔雀蓝宁绸棉袍,整个人看上去有点怪,见了人也还是有点僵,也不大有人跟她说话。”
即便是高度写实,依然透露出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矜持,她在没有恋爱前真是寂寞,难怪胡兰成要称她为临水照花人。一个人要度过这么漫长的尖刻、孤独、没人缘的一生,简直比她的小说更传奇。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金锁记》写道:“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如果不是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这篇小说刊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时任汪精卫组阁政府的文化官员胡兰成躺在庭院的藤椅上漫不经心地翻阅,骤然读到,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读了一遍又一遍。
摇曳多姿的文字,满纸氤氲的烟华,令胡兰成无从忘怀,他向苏青要了张爱玲的联络方式,想要去拜访她。
那时的胡兰成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总有人评述这段情事,以为他们的相遇好似朵朵饱满的孢子植物喷薄而出,从悲伤的原点出发,走向的是广阔的虚无。
却不知,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人可以抽离前尘往事,知悉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与她,是芸芸众生还在追求今生今世时,一块岩石与另一块岩石定下的生死契阔。亦是男女在天下人面前相悦,这样坦荡,又这样私情。情怀可以是这样媚,然而又真的是无情。他和她,是风流事,亦是家事,更是没有事,总总都是物心人意的珍重。
就像张爱玲未曾写完的《少帅》。在这部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为原型的作品里。少帅去了河南前线,赵四小姐和朋友过中秋节,她当然想念他,“两人走在电车铁轨上,直到一辆电车冲她们直压过来,整座房子一样大,当当响着铃,听上去仿佛是我找到的人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成为痴狂,连张爱玲都变得笨嘴拙舌。书中尚未完成的篇章,是关乎政治的宏大叙事:西安事变后,少帅被终身幽禁,国共两党的处境开始微弱变化,国家命运由此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张爱玲的意念里,也不过是为了成全两个原本没有那么笃定相爱的人。
可是,如果张爱玲没有意兴阑珊地搁笔,那么《少帅》应该还是一个色彩明亮的故事:少帅和赵四小姐举办婚礼时,两人已年过半百。宾客云集,教堂里满是鲜花和掌声,祝贺这一对生生世世的恋人。有人邀少帅致辞,他沉吟良久,对赵四小姐说:“你是我永远的姑娘。”
在爱情的光辉里,幽禁岁月也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这个故事里还会有许多温暖的桥段:在他们的寓所里,张学良打扮成跑堂的模样,系着围裙,戴着一顶厨师帽,一手执笔,一手拿着菜单,装腔作势地问赵四小姐想要点什么菜,而赵四偷偷地笑着,宛如回到了少女时代。那年,他们已垂垂老矣,然而一想到余生能执子之手,余生亦令人充满期待。他们避世隐居,安静地等待一场甜美的死亡。
这个未完的故事对张爱玲亦是如此,无论何种结局,他是否负了她,抑或是她在他患难时不够体谅他的苦楚。他们的故事亦如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所说的:“是我自己挤到你跟前,扑进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
胡兰成初次拜访张爱玲,她不见,这原是正常的。潘柳黛形容张爱玲的倨傲与古板,说:“若和张爱玲约好什么时间见面,去得早了或晚了,张爱玲就不会见。约定好了的,都未必可见到,何况不速之客!”胡兰成寻访不遇,留下张字条就走了,谁知隔了一日,张爱玲居然主动来到胡兰成居住的美丽园。
胡兰成的侄女青芸回忆初见张爱玲,言辞中满是挑剔和不以为然:“张爱玲长得很高,不漂亮,看上去比我叔叔(胡兰成)还高了点。服装跟别人家两样的,她是自己做的鞋子,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衣裳做的是古老衣裳;大家做的短头发,她偏做长头发。跟别人家两样的,总归突出的。”
然而胡兰成却惊艳了,却艳也不是那种艳法。惊也不是那种惊法。她的模样,超出了以往他对于女性美的所有体验与想象。
寻常女子的美是春天吹落的桃花瓣,是仰俯可拾的艳丽,而她的美却是卓尔不群的。她的性格是尖锐的,好比是麦芒轻轻蜇在手掌心,有那么一点点疼,还有那么一点点隐秘的快乐,在众多中庸的女人中,她的风情令他别开生面。
他深深地陷在对她的迷恋中,从她家出来,去朋友家串门,一桌子人在打牌,他在旁看了一会儿,只觉得心里满满的,旁人在说什么做什么他恍然未知,于是走到门外的春夜里,继续想她。她就像一尾鱼,活泼泼地游来游去,总归是游在他的心里。
三
三十年在一起,比爱情更清澈,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纹理,你了解我的诗行。
——茨维塔耶娃
胡兰成形容清末以来的革命委决不下,用《诗经》里写女子打扮去游春的篇章来作譬喻,女子央请良人在房门口等等她,在楼下堂前再稍为等等她,一面尽问:“我戴的这付白玉环子,配上鬓际的白玉花好吗?我戴这付翡翠的,来配绿玉花好吗?”而门外浩荡春光亦真的都在等他,因为吉日良辰要有他才有主。
虽然,他们爱情的生发是如此不合适宜——在旧上海沦陷区,一个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与汪伪政府的文官——看上去是那么的不搭调。然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是好。
秋天栗子上市了,栗子铺里的师傅拿着一柄铁铲炒栗子。铁砂子蹭到铁锅边缘,发出“啦啦”的声响,那是砂子们在快乐地歌唱。热腾腾的栗子香气里还挟裹了桂花甜腻的香味,热栗子用牛皮纸裹住握在手上,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暖意。张爱玲爱吃栗子,还喜欢拉了胡兰成去街头品尝各色美食。
他为她离婚了,那年他的儿子胡纪元才5岁,印象中还是父亲离去的那个初夏:他在门口玩耍,父亲带了一包小荷叶回来,那日中午,家里做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是初初萌生的,很小很小的叶片,青铜钱一般,一汤匙可以舀起两片。父亲说清水小荷叶汤又清香又消暑,喊大家都来吃。他说父亲是慈爱的。年长后,父亲客居日本,他犹记得父亲爱小荷叶,想要山迢迢水长长地寄了去,父亲却不肯要。
那时候的胡兰成是真心爱张爱玲的,他为她舍弃了大家庭的温暖,只为与她一起过饮食男女的尘世生活。
他向她求婚,一扫往日的疏狂:“我本自视聪明,恃才傲物惯了的,在你面前,我只是感到自己寒伧,像一头又大又笨的俗物,一堆贾宝玉所说的污泥。在这世上,一般的女子我只会跟她们厮混,跟她们逢场作戏,而让我顶礼膜拜的却只有你,张爱玲,接纳我吧。”
目下无尘的张爱玲又怎么会爱上俗物与污泥?胡兰成典则俊雅,温润有方。他著文,更是倚马可待,稿成,极少改动。办报时,社论均由他亲自执笔,文笔犀利,每令报纸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进而被抽起不发,又无预稿替补,遂留白。同仁规劝其稍事隐讳,他答: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办刊之特色。
他与她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起的每一个话题,都汁液饱满,魅惑丛生。他们在一起的辰光,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谈及文学艺术,他每念一句,而她的解读则赋予辞章新的含义,每每令他若有所思,醍醐灌顶一般的通透;而她亦赞叹他对她的知与解,他描述的她,亦有了新的形象——花非花,雾非雾,如“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如衣箱里的华丽深藏。
他是真的懂她,他拿颜色来譬喻她的文章,说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人人皆以为她的文章是道不尽的苍凉,只有他石破天惊地说:“爱玲极艳”。他说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一样面对人世间的美好,但只有他才惊动,要闻鸡起舞。就譬如“心爱一个人的文章,对这个也说,对那个也说,像孩子心爱他的玩具,睡里梦里都惦记着,一早醒来就在被窝里找它”。她当然也知道他是最知道她的男人,“好得不能被用来做选择”。
他见她低眉顺眼地坐在自己跟前,夸她谦逊,她反过来赞他:“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们之间的懂得,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情,更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深度融合与碰撞。
她亦崇拜他,在热恋中,“他走后一烟灰缸的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
她说他“眼里的光采像捧着一满杯的水” 。当“他迎上来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着他的腿,脸贴在他腿上”,“过了童年就没有这么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
她和他相对而坐时,只管看着他,喜不自胜,用手指着他的眉毛,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儿我喜欢。”真的是喜欢极了,她轻轻地唤他:“兰成。”她还反反复复地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真的么?”为同一个答案问上一千遍。
胡兰成喜欢桃红色,他说:“桃花极艳,那颜色亦即是阳光,遍路的桃花只觉阴雨天亦如晴天,傍晚亦如晓日,故艳得清扬。”张爱玲便穿着“能闻得见香气”的桃红旗袍、绣了龙凤的绣花鞋子,每次他从南京回来,她就这么穿着,单穿给他一人看,幸福原就是这般镂金错彩!那时候的张爱玲,就仿似一朵没缘由沾了衣襟的桃花,只为他一个人,自顾自地盛放。
某夜,他们芙蓉帐暖度春宵。清晨醒来,她有些难为情,担心被姑姑听见,要他拎着鞋子蹑手蹑脚离开。
长长的客室,稀薄的阳光从玻璃门射进来,不够深入,飞絮一样迷蒙。他穿上皮鞋掷地有声穿房而过,每一步都重重踏在她的心坎上,她躺在床上,既忐忑又欢喜,心里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
那时候的日子,是一满杯的水,满得要溢出来的幸福,虽然偶有小别扭,也像是《海上花列传》里沈小红和王莲生,两个人闹别扭,沈小红抹眼泪,王莲生愁肠百转,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浮华奢靡的故事背景里,生出的是又甜又腻肉身的快乐。
然而爱情到最后,拼得都是人性。这世上终是没有完美的事物,万事万物都是有期限的,随着岁月的侵蚀,终是要风化,美好一层层剥脱,余下的是苍凉的底色。他有他的弱点,他一生都怀抱热望,却一生都在半途而废。他是个矛盾的人,亦是个不坚定的人,宛如他的书法,建立在两种极端矛盾的用笔趣味上,既北碑般的浓重,又纤细如游丝;既艳丽,又威猛,呈现的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机巧。
往后的一切,就像爱尔兰那个特立独行的女歌手西尼德奥康娜在歌中唱道:“人生路上风大浪急,总有伤害潜伏如猛兽窥伺,总有机会让你蹲在角落,在橱窗里反观自己痛哭流涕。”
当歌手拨动琴弦,阖上眼帘,低声浅唱时,往事在夕阳的余晖中呈现:那些撼人心魄的情话;那些散漫美好的岁月;从相见到别离,从清晨到日暮。那个开出花的张爱玲全然不见,连同那些在一起生活时繁盛的细节:深深庭院与繁花、雪白的手剥开微金的橙子、新绿的茶叶在水中缓释余芳、端丽细致的菜肴、一意孤行的春天褪去了曾经桃红配葱绿的妖娆。
就好比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摹的景象:一个患了失忆症的村落,人们对世间万事万物早已忘情,却对文字仍不能忘怀,家中物件俱贴上小纸条,用文字注明物品名称、用途,才知如何使用。那样的余生像日薄西山的落日,微弱的光芒再无一丝暖意。
四
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忘却一种我供养不起的幸福。
——小仲马
庄子讲过一个很古老的故事:水干涸了,有两条相爱的鱼相互用嘴里的空气和泡沫来湿润对方,只为了能让对方多活一秒钟。然而水终将漫上来,与其用唾沫让对方多活一秒钟,不如让对方回到大海中快乐地游弋,哪怕是它从此不再惦念往昔的岁月。庄子伤感地慨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夏天的一个傍晚,西边天上余辉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两人站在阳台前眺望,胡兰成对她说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张爱玲对他说:“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她还对他说:“你变了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弯弯绕绕的语气里,不知隐匿了多少瓜瓞绵绵的情意。她还对他说希望战争不要结束,那话听得胡兰成都生出了微微的诧异与不适,但她心里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就像她在《倾城之恋》中那段写白流苏的心事:“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张爱玲所有细细密密的心思,都借了白流苏说了出来。
胡兰成先是去了武汉,在汉口办报时,和楼下17岁的护士小周好上了。小周性格温存,胡兰成说她的人像“江边新湿的沙滩,踏一脚都印得出水来”,小周送张照片给胡兰成,题上乐府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胡兰成就这样坏了小周的心。
离了武汉,胡兰成又逃亡去了温州。张爱玲“千山万水的找了去,要和他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她对他说:“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胡兰成与范秀美早已成了夫妻,胡兰成住在范秀美家,却将张爱玲安置在旅馆,对外宣称是妹妹。
三人在旅馆见面,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感到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才是胡兰成的亲人,而自己,倒是外人了。
那微妙的情态,就譬如《红楼梦》里黛玉与众姐妹正说笑,偏是宝玉留心,他使个眼色儿,黛玉便进去一回照照镜子,原来是鬓际松了,这就因为是自己人。
胡兰成评说:“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然而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胡兰成又说了句自相矛盾的话:“凡好东西皆是家常的。”
多少年过去,张爱玲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然终结。“张爱玲”这三个字已成为某种符号或是象征。每当人们谈及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旧上海的萧瑟的秋风、迷朦的月色、黄包车、红木家具、青花瓷,织锦缎靠垫、周璇旖旎的歌声,还有昏黄的汽灯,微甜红酒、老公寓、老门牌、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像月份牌、咿咿呀呀响起的胡琴声……这些林林总总的物什,样样都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怀想与袅袅情丝。
然而,不朽的张爱玲终是败在了家常里。胡兰成赞小周洗件布衣亦洗得比别人洁白,烧一碗菜,捧来亦端端正正。小周帮他整理行装,样样都细心折好放好。胡兰成亦赞美范秀美,在家烧茶煮饭做针线,堂前应对人客,溪边汲水洗衣,地里种麦子收豆拔菜。她烹调小菜,不过是一碟炒鸡蛋、一碟豆芽、一碟吹虾、一碟麻蛤。两人相对而坐,范秀美满心欢乐,胡兰成亦觉得心里感激。
在小周和范秀美面前,张爱玲忽然变得不自信。她在《色.戒》写道:“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她以为她缺少这个通道。她那枝千娇百媚的笔,放在生活里,只是徒具色相,却失了本真。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同去温州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织工场,他们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胡兰成叹道:真真的是如花美眷,如水流年。
然而属于他俩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终是要隔了距离去看才觉得好。就好比是帝王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人向里窥探一下,身上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惝恍的戏台的辉煌里,越发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
乱世中逃亡的胡兰成,走到天涯海角,他要的只不过是一个着实的亲人。
然而,张爱玲却不是。他说她“一钱如命”,他还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 。
他这样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向来擅长借他人团扇,说自己秋凉,亦擅长在事件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中,寻根究底。然而,在自己的故事中,她却迟钝了。
她自小就被过继给伯父,称自己的母亲为二婶。父母离异,母亲环游各国。当她逃出父亲与继母的家,来到母亲家,母亲却嫌弃她,这使得张爱玲长久地不安。以至于心心念念要把母亲供养她的钱都还清。她最大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胡兰成怜惜她,给了她一箱子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等待她的母亲归来。日本投降后,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也知道他需要钱,然而她心意如铁,吝啬得令人难堪,她的理由是: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
他爱她,无论他之前或之后爱过多少女人,但最爱的一定是她。然而,她真的不是那个贴心贴肺的着实的亲人,她不过是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一如她笔下《创世纪》中的匡潆珠,毛耀球对她有好感,于是与她搭讪,想邀请她看电影,潆珠淡漠地摇摇头,笑了一笑。他站在她跟前,就像他这个人是透明的,她笔直地看通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一种荒漠的神气。
五
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博尔赫斯
临别前,两人走在曲折的小巷里,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小周或是范秀美,他都不会放弃,她们带着俗世人间烟火的气息,还有踏实的温暖。他对她说:他待她,“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他举例说:小时候父亲分金橘给他的表兄弟姐妹们,唯他无份,他心里很失落,一转脸,到没人处,他父亲却拿出一个红艳艳的大福橘给他,他待她,亦是如此。张爱玲叹道:“你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三十年以后,她韶华已逝,她回忆起年少时的心情,开始动手写《小团圆》。她写他们的决别:“有时她望着沉睡的他,黄黯的灯光中,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像在黄昏时分出海,路不熟,又远;她会觉得他的眼睛有无限的深邃,但是又想,也许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他神秘有深度。她这样依依恋恋,绵绵延延,但于某日一早,睁开眼睛,双臂围住他颈项,轻声喊他的名字时,却觉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
她还写她对他的恨意,她对他说,自己因他很痛苦,她将一切归结于自己太爱他,所以思念他,妒忌他身边的异性,失去自信心和斗志。她叹道: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他微笑着回应:“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说:“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只保留他所拥有的。”她说她的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又一夜。
她为之消瘦,靠喝西柚汁维持生命,她靠在藤躺椅上,泪珠不停地往下流。他在她家过夜,背对着她。她竟然想到:“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
但她真的很爱他,她移居海外,多年以后,她梦见五彩片《寂寞的松林径》的背景,青山木屋蓝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松林里出没有好些个孩子,都是她的。然后他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她惊世骇俗地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沧海桑田以后,她还记得,有天晚上,“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的袖子里的手臂很粗”。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肉身感一直跟随着她。因爱生出的疼痛依然处处可见。
那些文字就像是一纸金纸折扇,记录下绝色年华,那是她写给已然消逝的时光的一封情书。谁都一样,一直在丧失,在别离,就像夜里飞过的萤火虫,就像隐秘的根须从土壤中剥脱,就像夏季的蝉鸣,从此后一去不复返。
不用等到老去,胡兰成已经在追忆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他不是浪子,但即便是浪子依然有真情。西庆门失了李瓶儿,身边纵有如花美眷,见到眼里,都是死去六娘的影子。点戏“我只要热闹”,听了两句居然落泪。郑爱月为了宽慰西门庆,亲手给西门庆“拣”一道名为“酥油鲍螺”的点心,旁人吃了大赞,只有西门庆说:“我见此物,不免又使我伤心,唯有死了的六娘,她会拣,她没了,如今家中谁会弄它?”
他也写那场诀别:他找到她那儿去,她已然搬家。他怅然坐电梯离开公寓,隔了铁栅栏,看电梯一层层降落,仿佛没有尽头,恍惚如梦。他说他仿佛是横越三世来见的,而她却不在。话语中带着刻骨的疼痛。他在虚空中追问:“那一屋的华贵随你到了哪里,那一层金黄的阳光如今移居到了哪儿,还有那随风翻飞的蓝色窗帘遗落在何处?”
然而她终究是不再回答了。
他还写他对她的爱:逃亡武汉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她的肉身感也一直伴随着他。他说有次去戏院看戏,回来时下起了大雨,他们就叫了一辆黄包车。放下雨篷,她就坐在了他腿上。虽然她生得高大,又穿着雨衣,当她娇嗔地坐上来时,他虽觉得诸般不宜,却也承认,那“真是难忘的实感”。
他却从未书写过对她的恨。他只说,收到她的诀别信,信中还随附了30万元钱,却不谈其他。然而她却放不下,她在《小团圆》里说这只是还债,只因之前他给了她很多钱,仅此而已。
时间是湮没一切的幽深海洋,在万千时光流转之间,那一场诀别永久地镌刻在光阴里,那些痴狂的、忧伤的岁月,宛如波涛汹涌,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静寂里。
他们在一起那三年,月色一样迷人,需要用长长的一生去怀念。他们的笔尖落在纸上,字句像藤蔓肆意生长。爱亦像藤蔓爬岩走壁,那些文字剖开内心深处的隐秘,留下耀眼的篇章,也留下灼目的痛苦。
六
若我会见到你,事隔多年。我如何向你招呼,以眼泪,以沉默。
——拜伦
张爱玲去世后,《小团圆》违背她的生前意愿出版。像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漂流瓶,历经沧桑,在时间的河流惘惘然漂泊了许多年,它想要送达的主人永远也收不到这封献给时光的情书。后来人捡到重新打开,悉心封存凝固住的时间如琥珀一般:真言在笔尖沉落,层层叠叠的心事,甜蜜的颤栗、相处的温存、静默的等待,深刻的孤独……往昔种种,回旋在脑海里如同光影一般繁复、幽曲、莫衷一是。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座精巧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沦陷在时光的泥沼里。
世间的情爱,好比潮水和沙滩,有的是在不断的冲击和拍打中愈发深刻,而有的却在这过程中偃旗息鼓,再无声息。然而长相厮守并不是爱情的唯一归宿,木心说: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
这一切,胡兰成全然明白,有一次他写信给炎樱说:“她是以她的全生命来爱我的,但是她现在叫我永远不要再写信给她了。”
他回上海来打电话给她,听到他的声音,她会突然一阵轻微的眩晕,安定了下来,像是往后一倒,靠在墙上,其实站在那里一动也没动。
即便是近在咫尺,那又如何?那些争奇斗艳的市井食肆依然还在,只是她不会再拉了他去品尝;水面倒影中的万家灯火也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共同守在同一盏灯下。他再也不可能见到她,重新握住她那瘦弱而清凉的手。
她就这样自我耽溺,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她是个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她自己。
暮年的张爱玲,独自蛰居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每逢读《金瓶梅》,读到李瓶儿临终那一段时便纵声大哭:李瓶儿的孤绝无依,在西门大院中并无半个亲人。那时,她应该想起了他,想起他们初次见面,二月末的天气里,他们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他们,好得宛若已经多年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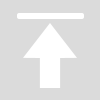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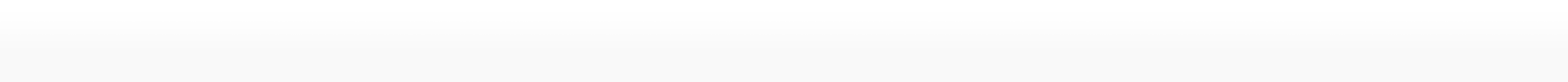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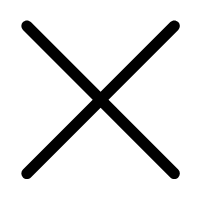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