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1年,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在苏富比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上意外发现一件藏品,那是一箱书信,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其侄子朱利安·贝尔、凌叔华以及其他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间的书信。拍卖目录写道:“凌叔华通过朱利安·贝尔进入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贝尔1935年在汉口任教期间,与凌叔华产生了一段私情。”那简约动人的笔墨,仿佛是在清扬寒冷的空气里,忽然间看到一间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的温暖屋子,女主人公香艳美丽的模样令人凭空想象,宛如董桥在《橄榄香》中描摹:她的锁骨是神鬼的雕工,神斧顺势往下勾勒一道幽谷,酥美的一双春山盈然起伏,刹那间葬送多少铁马金戈。
这箱书信令帕特丽卡·劳伦斯欣喜若狂,她坦言自己通过这些书信“走进重重迷雾包裹下的某种关系”,揭开了一段中西文学交往中尘封已久的情事。她后来更由此为基础,写成了研究著作《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勾勒出英国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新月派的文化往来交错。
帕特丽卡·劳伦斯在她的专著里郑重地写下一行字:“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有着闪光的价值。”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的情事当然是蜚耳的流言,然而更有史实佐证绝非虚妄的传言。那段情事中的人已然销亡,物亦破败。帕特丽卡·劳伦斯的这本书就像是一束蘅芜草——东方传说中的怀梦草,具有召魂的魔力:李夫人香消玉殒后,汉武帝念念不忘,为遣主忧思,东方朔呈怀梦草给君王,那日夜晚,李夫人果真翩然入梦,武帝醒来,衣枕犹有异香,历月不散。
往昔就在那气息中悄然复活,一如灵魂,以丝丝纤柔几乎无法觉察的存在,强韧地荷载着已然消逝的记忆。
二
1935年10年,在画家母亲瓦内莎·贝尔和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鼓励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第一后裔”朱利安·贝尔坐了3个月的船,来到了武汉大学任教。
朱利安·贝尔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甚获佳评,他注定要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知识精英。那年的朱利安·贝尔27岁。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政局动荡,被历史学家称为“极端世纪”。朱利安·贝尔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讨论世界的前途,他信奉一句极端的格言:“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世界。”他怀揣着“中国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的革命激情来到中国,他甚至有牺牲的打算——预先写好遗书并预备了氰化钾。
然而,他却意外遇见了她——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凌叔华。那年的凌叔华35岁,人皆称她“珞珈山美人”。她的美在照片中是无从寻觅的,不过张爱玲早就说过:“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狼籍的黑白的瓜子壳。”
然而,透过那狼籍的瓜子壳,纷纷的岁月还是会被一一还原。
譬如,与凌叔华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向来挑剔,那时苏雪林的作品风靡大江南北,杨绛说她的母亲在每晚临睡前,总要读上几页苏雪林或是张爱玲的小说。可她对于凌叔华却是欣赏有加。她说凌叔华:叔华固然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儿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的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泰戈尔亦对凌叔华赞叹有加。1924年晚春,泰戈尔访华团齐聚凌府后花园,凌府别具心裁地备下数百枝刚采摘下的玫瑰、紫藤花饼以及石磨磨出的杏仁茶。紫藤花饼是用藤萝花加了脂油丁和白糖拌匀清蒸,饼色暖红,芬芳清冽,春情动人,又被唤作春情饼。那种机巧,使得泰戈尔忍不住私下告诉徐志摩: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凌叔华由此进入新月派文化圈。
三
1999年,旅英女作家虹影以朱利安.贝尔及凌叔华情事为蓝本写成备受争议的《K》,她在扉页上写道:“一切都怪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是空的,它那么容易与你相融,好像水倒进水里。于是我们在某一天,就成为一本书的纸和字,无法剥离。”
这本小说等同真人真事,处处充斥着香艳场景的描写,然而虹影有理由这样描写,她花了大半年时间研读关于朱利安.贝尔的信札与史料。朱利安.贝尔在与母亲通信时谈及凌叔华露骨地表达:“亲爱的瓦内莎,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他写信给伍尔夫,称自己“爱恋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所以虹影也有理由这样揣想:是她将他引入爱情的繁花秘境,她的身体犹一封匠心独具的情书,身体迤逦的线条在他眼中熠熠发光,她甜蜜的情话听来坚定纯粹,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体验到东方式神秘的爱情,充满新鲜和仪式感。
该书的出版引致陈西滢与凌叔华女儿陈小滢的极大愤慨,认为侵犯了亡者的名誉权,将虹影诉之法庭。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处境的人的理解中是如此的迥异:像是偶尔重叠又遽然分开的身影,又像是遍布镜子的房间,尖锐无穷地彼此映照着,充满着延宕与折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烈焰,一半是天真与洋洋自得,一半是愤怒与无从宽宥。
在俗世的价值观中,通奸是一个通以启齿的话题。然而,福楼拜却武断地断言:“所有的名著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通奸其实蕴含着极其复杂的人性的和历史冲突的意义。当通奸这个行为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含量,其虚妄性也显而易见。虹影讲述的这个故事,不过是复述爱情的甜美与残忍,就像一篇俄国小说的开篇:尽管白桦树梢光秃秃的不见一丝绿意,但那饱经风霜雨雪的树皮下,脉管里的汁液如春潮一般奔涌着,太阳晒暖了枝头,鼓胀的柔荑花序正欲挣脱鳞片的层层包裹,吐露芬芒,生命版图被重新打开,历经一番轮回,最终来自于尘土,归根于土地。
又或许可以说,在每一个女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在婚姻中,曾经的自我被长期湮没,于是寻找一切绝望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就像是手里一条迸跳的鱼,又想抓住它又嫌腥气。虹影的那本书,就是那柄凿开心中冰海的利斧,她钩沉人物命运,重访历史的坚硬与轻柔,捕捉历史中的戏剧性,深入其中的肌理与细节,那些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体现出让人动容的温度,令人低徊不已。
四
作为生长在富贵之家的知识女性,凌叔华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出尘、任性、不羁和自由。
在未遇到朱利安.贝尔之前,凌叔华的前半生波澜不惊,一如伍尔芙描述简·奥斯汀那样:“她降生的时候,一定有一位仙女来到摇篮边将她高高托起。当仙女把她放回摇篮时,她就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王国,她欣然接受天意,愿意成为这个王国的主人,放弃对其他的一切欲望。”
直到1935年10月,长夏已然过去,武汉溽热却尚未完全褪尽,珞珈山妖娆万状,朱利安.贝尔安抵达武汉大学当天,就去了的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家。陈家住在武汉大学著名的十八幢,那是一座英式别墅群,共有十八幢,陈西滢家住在第二幢,恰在半山腰,别墅座落在珞珈山南麓,远眺是浩淼的东湖,空气温润却不寒湿,天睛的日子,太阳由东南升起,又从西南降落,别墅一整天都笼罩在薄纱般的阳光中。郭沫若给这座别墅取了一个甜蜜的名字:蜂窝水涡。
当朱利安.贝尔拾阶而上,山中落叶铺满小径,而长青藤则爬满石墙,石径上有隐隐的青苔,而大朵大朵肥嘟嘟的蘑菇散落在路旁。
在陈西滢家,他遇见了院长夫人,看上去很甜蜜的女人——凌叔华。他晚上写信告诉母亲:“整个下午我都和文学院院长一家呆在一块,有他的妻子,还有他六岁的女儿——非常可爱迷人的小女孩。我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简直是内地的剑桥。”
在朱利安.贝尔眼里充满东方情调的武汉,在凌叔华眼里却枯寂无比,她写信给胡适说“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她还说“武汉三镇竟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
命中注定,她会遇上朱利安.贝尔,他令她看到了爱情暗黑的基调,却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甜美,宛如罂粟一般,邪恶的冶艳中透露出无尽的欢愉,她注定在劫难逃。
五
1936年的冬天不再是“愔愔的白过了”,很快,朱利安.贝尔承认爱上了凌叔华,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她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
朱利安.贝尔喜欢给自己的情人按字母顺序“编号”,凌叔华是他的“K”,即第十一。
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恋情产生的契机缘于陈西滢的一次外出,日寇企图侵占故都的消息不绝于耳,凌叔华惦念北平的母亲,她来到朱利安·贝尔住处寻求安慰。朱利安.贝尔写信向母亲描述:“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没有爱过……整个氛围就像一本俄国小说……”
就像波伏娃爱上纳尔逊,只用了两天两夜。在一起时恨不得合抱成木,通过对方的温度完成对世界的感知。纳尔逊去服兵役分离的日子,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通过手指触摸笔尖的温度完成对爱的感知。
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爱恋亦有那么炽热。他们密谋去北平幽会。凌叔华籍口去探望她在病中的美国朋友克恩慈女士。于是他们分头上路,凌叔华先行去北平。火车兴兴轰轰地开了一夜,清早醒来,凌叔华迫不及待地给朱利安·贝尔写信:“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冬天的风景真美,我很高兴再次看见辽阔的平原,平原上散布着的雪白雪白的积雪和枯黄的干草……啊,我多么喜欢华北!多么美的世界!”那封信依然延续了她一贯闺阁派的风格:深藏不露、深情款款,笔底却有着隐隐的风云,每一个字都躁动不安。
凌叔华将朱利安.贝尔安排住在一家离凌府不远的德国旅馆。那些时日,她陪伴朱利安遍访北平古城,朱利安.贝尔写信告诉母亲,年少轻狂跃然纸上:“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些地方如同巴黎一样奇特。能想象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还要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地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品味无可挑剔,她是世界上所有罗曼蒂克男人的梦想。……我去剧院,去溜冰(很差劲,冰也不行),还作爱。……”“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凌叔华烫发、化妆,她摘下眼镜,穿着裘皮大衣,戴着裘皮帽子,看上去时尚俏丽。还在一天晚上,她在家里为他做了一道甜菜汤。这亦暗合了朱利安.贝尔心中的东方情调,就像是唐代王建写的《新嫁娘词》中描绘的情境:“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朱利安.贝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总的来说,她在床上表现平平,但是除此之外她真是迷人。”
即便深受布鲁姆斯伯里开放性观念影响的瓦内莎·贝尔,亦担心在古老的中国他们的通奸会有风险,而朱利安.贝尔却请母亲放心。他与凌叔华曾谈论过是否要结婚,但他俩谁也没有真正打算要走到那一步,不过双双同意他们在武汉继续保持情人关系。
在那段情事中,凌叔华与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
但那时的凌叔华是欢喜的。胡兰成曾说:“唯有女子的欢喜,方可与天地不仁相匹敌。”然而谁又能与天地不仁匹敌?即便是仁慈的上帝亦不能。正如圣经所述: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后,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怒斥道:“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随着夕阳的沉落,世界的一切荣光也渐渐地消失,女子的欢喜既莫能外。
六
从北平回到武汉,那段甜蜜的日子仍在继续。朱利安·贝尔每天上午将佣人们支开,打发他们去干各种活儿,凌叔华在那个空隙悄悄来到他的住宅。
这段爱恋春水初生时,朱利安·贝尔认为凌叔华性格中“敏感”以及“有时还有点使坏”的特质,随着情事的深入,“敏感”则变成了暗黑性格的基调。而“有时还有点使坏”则成了深沉的心机。东西文化的差异,使得这段情事举步维艰,陷入滞涩的僵局。
凌叔华开始竭力阻止朱利安·贝尔会见其他女性朋友,阻止他去参加所有未曾邀请她的聚会。
而朱利安·贝尔原本是拜伦式的英雄,在情事上收多放少。布鲁姆斯伯里浪漫叛逆的思想更是浸染到了他的骨子里。他思慕神秘的东方文化,然而不免有些叶公好龙。他不知道,在传统东方文化中,无论是信奉什么,儒教抑或是道教,都是不过是东方民族中交替的情调,东方式的自由,不过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看似胆大妄为,头上的紧箍咒就是齐天大圣自由的极限。
他用西方的价值观爱她,她却按照东方式的传统为这段情事奉献一切,比如自由,比如婚姻。他为此不堪重荷。他们俩就像两个相邻却不贯通的湖泊,彼此听得到波涛的喧嚣,近在耳畔,却永远无从交汇。又仿佛是孤儿院的两个孤儿,看似形影相吊,却永远无法血脉相连。
而对于她而言,她为这段情事承受巨大的压力,周围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家庭的指责。她舍弃一切并尽力而为,然而最终换得的还是无所适从。在她的价值观里,她与朱利安·贝尔非黑即白,永远没有中间地段,她未曾懂得适度才是保一生平安喜乐的制胜大法。她的东方情调如此吸引他,她却未曾从古老的东方智慧找到答案——譬如《易经》,如何依从并摆脱因果之律,最后在因果之律不可抵达的地方产生意想不到的幸运。这才是东方式的智慧与风流的极致。
而于他而言,他的姨母,游走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伍尔夫说过一句俏皮话道尽了他的尴尬: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到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
七
对于我们的生活,天才的伍尔夫还说过:“它不是一列列整齐排列的马车灯,相反,混沌和暖昧才是生活的常态,像一片光晕,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普通人。”
凌叔华陷入了这种无明之苦。无从解脱。她整夜整夜睡不着,只有凭借安眠药才能片刻从现实中消遁。她还买了一包鼠药,戏剧性地以自杀相威胁。在她的意念中,死亡是甜蜜的,它即将把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然而肉体的死是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未曾抵达,她依然要屈辱地活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无法逆流而上,无穷无尽的过往早已不见踪迹。
1936年10月31日,朱利安·贝尔写信告诉母亲:“她的丈夫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傻瓜的地位,他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提出了一个相对简便的方法来处理这场婚外情,叔华要么与他分居,但不是离婚,要么与他和好而与我彻底一刀两断。她选择了后者。我打算辞职,以便减少紧张气氛。而我的家人是不会希望我是因难以言明的理由回国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是因政治原因而回国的。”
作为那段情事的收梢,朱利安·贝尔曾写过一首诗致他的爱人:
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的爱人在她那冰冷的被窝里入睡
她的脑海里追逐起种种幻影
窗外的风将窗帘卷起层层波浪
回到英国后的朱利安郁郁寡欢,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想着心事。他忽略了身边绝美的乡村景致:教堂、小鸡和散步在青草地上白色绵羊,海湾边呜咽的水鸟的叫声,如同耳语一般,路上遇到一些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双方互相点头致意。于他而言,生活是危险的,世界是荒芜的,决定去西班牙参战是他唯一也是最终的解脱。
虹影曾叹息说:朱利安一辈子的毛病,就是感情生活中的 “负心人”(Heart-Breaker)。
尽管如此,虹影还是全力温柔地讲述这个故事。虹影说希望她本人就是书中化名为“林”的那名女子,她期待与朱利安.贝尔“相遇”。在小说完成后,她重访查尔斯顿农庄,在瓦内莎常坐的长椅上怀想朱利安,一如当年凌叔华的思念。
又是一个温柔的夜晚,虹影将自己潜入“林”的意念中,用“林”的口吻写了一首诗给朱利安,那首诗一点也不暖和,诗里满是“林”飘忽不定的惊魂和女人的灰:
古琴台——惊闻你有R后
“他带我去跑马场”
那个英国女子很漂亮
好像心也不错。
古琴台只有我一人,
我是那遥远时代的弹琴人,
而你听不到。
听到你也不明白:
东方音乐讲的是单调的韵味
寒风迫使我下山,
下山是我惟一的路。
凌叔华又何尝不明白,当男人彻底懂得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朱利安.贝尔离去后,25岁就凭籍小说《酒后》一举成名的凌叔华,余生不再写作。
八
1937年7月18日,29岁的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前线驾驶救护车时被炮弹击中,弹片深嵌胸腔,不治阵亡。
凌叔华和陈西滢依然维系着他们的婚姻。1946年后,陈西滢常驻巴黎,而凌叔华带着女儿,住在一海之隔的伦敦。晚年的陈西滢沉默寡言,有一次,女儿陈小滢问他:“为什么还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陈西滢说:“她是才女,有她的才华。”说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陈小滢回忆往事,有句话说得意味深长:“母亲的一生一直都在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她说父亲很喜欢她,经常给她写信,每次都称其为滢宝贝,句句鼓励之情。却鲜有来自母亲的拥抱,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次母亲给她洗手时说了一句温情的话:“洗小猫猫手。”
然而即便是“包裹的严严实实”,亦是千疮百孔。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不千疮百孔,然而纵是千疮百孔,也是感情。有的感情千疮百孔不肯放手,有的感情千疮百孔未曾形成就戛然而止。
朱利安死后,瓦内莎有近一年时光都无法提笔作画。瓦内莎在1940年3月写信给凌叔华:“近日,常在这个时候想起你和朱利安。三年前,这个时候他回到英国,正逢春天的到来。这是多么的枉费——他看不见春天……”
在伍尔夫和凌淑华的通信中,亦常常提到朱利安。伍尔夫的信一如她的小说,视线异乎寻常的澄明,但似乎总是隔了一层玻璃,永远不触碰任何东西,她淡然写道:“我们的那条小河,小得如同一条大蛇,朱利安曾涉水过河,还在水上放一只小小的船”。有时,伍尔夫亦伤感万分:“我总在想,要是朱利安在,能帮助我就好了。”
九
1989年12月,耄耋之年的凌叔华,终于如愿回到了故乡北京。她在《爱山庐梦影》说:“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
倘若朱利安.贝尔还在,这句话,也可以反转过来说。
翌年5月,凌叔华离世,在弥留之际,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此刻的她站在路的尽头,老迈的头颅已无力抬起岁月的花环。然而只要他爱着她,她就永远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当年,她倾倒众生。当她老去依然如此。
在她死去的那一瞬间,古老的东方情调依然还在,在岁月中完成长情的守望,停留在他们初相遇的那一瞬:
“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高绾绿云,金簇小蜻蜒,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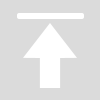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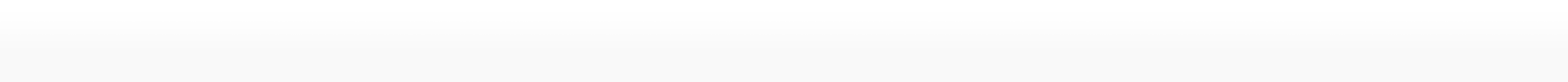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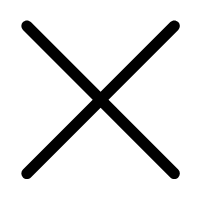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