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珍
1
中秋日,陪婆母吃过午餐,我照例去旺中旺超市选了月饼糕点柚子,去养老院看望董老师。
站在熟悉的门前,久敲无人回应,心中顿生不祥预感,随之周身过电般、心中一凛。
强按住心头不安,折回总台问询,惊悉董老师“已经走了”。
“请问董老先生是什么时候走的?临终有人在身边吗?”
“4月走的。通知了他的侄子到场。”
她的回答言简意赅。在养老院工作的人,或许早已惯见生离死别。
我还想问点什么,老公拍拍我的肩,语带安慰:“先生85岁,也算高龄了。回去吧。”
我心中感慨,总不敢相信。我也不愿相信——向来倔强的董老师“壮志”未酬,心愿未了,他怎么肯向命运举手投降,撒手西去呢?
2
时至深秋,阳光依旧暖暖地照在那方阳台。
阳台很小,密密匝匝地堆放着衣柜,书报杂志,生活杂物,干粮点心。阳台尽管逼仄,董老师依旧腾挪出一个小角落,摆放了一张小桌,旁边配了两张椅子。有时去看他,家中正好有现成的花,我会随意抽出几支,插进小瓶,灌上水,一路捧着,走进养老院,把这小小的花安放在这张小桌上。
“董老师你看,这窗外绿植如画,窗内点缀两枝小花,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啊?……”
董老师眼眉含笑,一边点头同意,一边热情招呼我们落座。
打过招呼,董老师一边抖抖索索、慢镜头似的将水果一个个放进小冰箱,糕点一一摆好码齐,一边照旧自豪地对邻床室友介绍:“我学生,你见过的,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去年12月底,我去看董老师,同居一室的那位抗美援朝老兵也还健在。92岁的老兵人高马大,头脑清醒,精神尚好,只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儿女成群,子孙满堂,儿孙生活条件都不算差,但都“没时间”照顾他,他就来到养老院,成了董老师的室友。
3
室内气味有些难闻,加上我认为董老师应多晒太阳,我通常选择在阳台上和他聊天。
阳台只两个椅子,董老师示意我俩坐下。老公坚持要站,我也一再把董老师“按”进有靠背的那把椅子。久而久之,董老师也就不再客气不再坚持了。通常是,我陪董老师坐着,老公站着,三人围成一圈,相聊甚欢。
董老师非常健谈。他博学多识,天上地下、从古到今皆信手拈来,从容驾驭。
和阳台相连的,是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放着两张床。董老师的床紧挨阳台,床边呈直角安放着他的书桌。董老师多年如一日在这张小书桌上阅读与创作。有好几年,另一张床闲置着并无主人,那床就常常成为董老师临时的桌子,用于铺陈展示他的新作。阳台门边堆着一摞高高的纸箱,纸箱边是个小小的冰箱,冰箱里有时是苹果,有时是香蕉,有时是柚子茶,偶尔有蜂蜜。这些都是他的朋友同事学生等送来的吧?他平日吃饭用的饭盒和筷子,也是放在这个冰箱里的。
夕阳依旧。照进他的阳台,照进他的房间。我一只脚跨进车内,还是忍不住伸长脖子透过阳台玻璃向里张望,发现不仅两位老人不见踪影,那些熟悉的家什杂物也统统不见了。我怅然转身。
打电话给良兄,确信董老师已登天界。
我十分黯然,去年12月底来看他还好好的,庚子新春疫情暴发,唯恐新冠病毒加害我不敢去看体弱多病的他。等到了端午,正忙着装修收尾,进家具,软装,搬家。谁料到中秋前来,斯人已去。熟悉董老师的脾气后,我知道陪他聊聊天是最好的关心,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只打电话问安。我曾数次“领教”过他对于只是“电话拜年”的朋友,语气中礼貌地冷淡:“新年好,哪位?……我现在这里有客人,方便时我们再聊好吗?”简聊几句,他便会挂掉电话。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在记挂着他。我也知道,他对于精神的追求远高于物质。朋友拎着点心水果前来当然很好,但他更看重面对面交流,思想碰撞出火花的快乐。那些与他交谈的人,眼神里流露出对他钦佩的、敬重的光,会让他忘却衰老和无力感,让他再次发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这种力量犹如一根稻草之于溺水者,及时拉他一把。
“大家去看他时别扎堆啊,一个个地去,更好。”我想,也许他孤独得太久了,窗外的暮色太辽阔了,他企图通过交谈时瞬间的热闹,来暖他因年迈与孤独而变得日渐苍凉的心。
我深为遗憾。不是遗憾他壮志未酬撒手人寰,而是遗憾自己因疫情等原因,未能在他弥留之际,给予关怀、陪伴与温情,让他带着温暖和希望离开人世。
“我们去送了他。别难过,你对他好,董老师心里是知道的。他走,也是到了年纪……”良兄安慰我说。
4
曾经,董老师在网上是颇有些名声的,也可以说是个“网红”。他2008年“触网”,开始学习电脑操作,学会了打字上网,还玩起了博客。他先后在网易、新浪、搜狐、新华网开通博客,将自己的诗与文传到网上,“吸粉不少,点击率迅速突破几十万”。
董老师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个聪明好学,性格倔强,也爱折腾的老人。“文学自古无擂台,老汉莽撞摆出来。”这个摆擂台的莽撞老汉,正是董老师。在文学上,他向来自负,却总觉得不受重视。眼看80岁了,顿感来日无多,故摆擂邀战——邀请国内外华夏文友逐项比试,“以了毕生切磋技艺与一决雌雄之夙愿”。
董老师经常在网络上流连忘返。写诗,聊天,交朋友。
那个虚拟世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生机勃勃又藏污纳垢。可是在董老师眼里,网络是可以将他射向天空的一支穿云箭,是可以渡他到理想国的一叶扁舟。这里也不乏温暖与真情。
看吧,“开擂”不到两月,与500余诗友“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写诗切磋之余,还认回俩干儿子。干儿子还不定期给他寄来一箱箱的糕点饼干,还有一位网友捐了2万元,帮他印了一本书。
5
“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于诗。”董老师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
我有幸结识董老师,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董老师就职于南昌市文联。“为往圣继绝学”,他开文学讲习班,办文学沙龙。少年的我常参加沙龙,就近聆听教诲。董老师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度儒雅。说到兴奋处,董老师目光闪闪,仿佛这世上有无数美好的事物正等着被记录,被创造。
只是后来,我惊讶地发现,满腹经纶的董老师仅有初中学历。他一生坎坷,工农商学兵,他都尝试过。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初中三年级的少年董本祺热血沸腾,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学校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他是家中长子,也是父母指望“光宗耀祖”唯一的读书料子。父母自是不肯,他就召开家族会议发表演说,对长辈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父母终于支持他如愿穿上了军装。他的光荣事迹,因《江西日报》的宣传报道,一时成为美谈。
参了军,他北上朝鲜未成,旋即随部队南下剿匪,九死一生,成为所在连队的唯一幸存者。
6
董老师幸存的不单单是生命,还有那些在硝烟暂歇、行军之余从随身携带的书籍中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思所想,得以在他的人生中溢出光彩。军旅期间,他曾在《长江文艺》《解放军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诗、小说、报告文学多篇。回南昌工作后,他所著并以“干戈”为笔名发表的《官经》《人鉴》曾风靡一时,被一再盗版。他还曾是南昌市首届滕王阁文学奖得主。
经商入伍,特定年代里三次被“打倒”,他仍未放弃文学理想。虽晚景凄凉,他的最大遗憾却并非困难无依的生活状况,而是自己的学问尚未获盖棺定论。
耄耋之年,董老师学会电脑操作,更倾尽全部精力和财产,用于著书、出书,哪怕是非正规出版,他也在所不惜。他希望把毕生所学留存下来,以期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洋洋洒洒500余万字,令我钦佩不已,感动不已。
无疑,他是带着某种悲壮离开他无比眷恋的世界的。说他眷恋,是因为他希望有时间留下更多的作品,供后人品评、评说与研究。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财富。
2013年他曾即兴吟诗一首,概括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
诗出名门实不肖,蛰居蜗壳度暮朝。
登山有志凌华岱,举笔无力颂舜尧。
高门深拥千重绿,旷野自逞一只娇。
春风不弃方寸地,花季欣然过断桥。
诗人已去,诗魂犹在。
7
工农商学兵的经历,铭心刻骨的战友情、同事情、师生情,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董本祺一一用文字记录,写进自传体长篇小说《人亦老》。而这陆续出现在他生命的人物,正沿着他目光所向,一个个成长为作家、诗人、医生、主持人,科长、处长、厅长……他们情怀温暖,联手用心用笔,书写并创造出一个历尽沧桑后更加美好的世界。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去年此时,在安静的养老院,董本祺老师在深秋的夕阳余晖里,微笑着挥手,目送我们远去。当我摇下车窗回望,他孤独的身影还在薄阳里,孤单单、怅怅然地笑着,目送我拐出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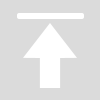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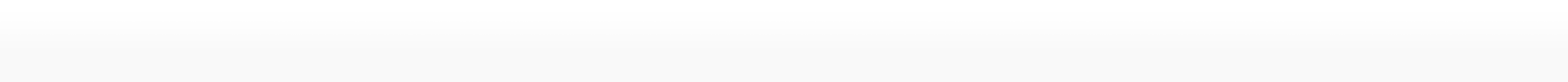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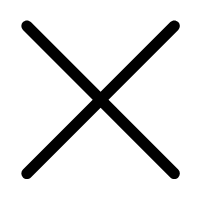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