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红土地上的脱贫报告》一书
傅玉丽
从景德镇市出发,上高速,虽然1个多小时之后便进入浮梁县西湖乡磻溪村。可中间过了一个隧道又一个隧道,1、2、3……一连8个,山区的特征凸显出来。刚到磻溪村前,便见一座高大的人物雕像立在村口,上穿旧时长衣、神态怡然。雕像上文字显示是村里清朝时第一代茶王汪宗潜。
进村便见茶王。浮梁果然名不虚传,到哪里都离不了一个“茶”字。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相信这句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为浮梁茶最早的广告。江西浮梁县自古出茶,最早从汉晋时代这里就开始种茶,而且品种众多。在唐代,就可见“浮梁歙州,万国来求”,当时茶叶产量进入全国前列。南宋时,这里与湖州、杭州一同成为江南三大茶叶集散地。
历史上除了诗人白居易,还有另一位大文豪,即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对浮梁茶情有独钟。他曾应浮梁县令之邀,来浮梁讲学。到浮梁后,品尝了当地茶、欣赏了当地瓷器,非常激动,不由地写下了著名的《浮梁县新作讲堂赋》。里面就有:“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如水玉;亦系其钧,水候是足。”之句。在此赋中,他不吝笔墨,充满深情地对浮梁之茶与瓷,给予直接点赞。
磻溪村位于浮梁县西湖乡北部,距浮梁县80余公里,与安徽省祁门、东至交界,山的另一半就属于安徽省了。磻溪村和紧邻的桃墅村从前一直就是浮梁北部的主要茶叶生产、交易集散地,当地村民茶叶收入,曾占到当时总收入的80%;其产出的功夫茶在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至清代末年到民国时期,村里茶叶商号竟达24家之多。兴盛时,曾有“磻溪茶不到,上海茶市不开”的说法,解放前这里还被称为“小南京”。磻溪村作为浮梁县古村落之一,至今还留存着一座全西湖乡唯一一座“益元祥”老茶号的房子,那就是村前雕像茶王汪宗潜的茶号。现在,这里的村民基本上还是以茶为生,有的世代制茶。
进得村里,只见村子房前屋后挂着的路灯,上面全写着一个“茶”字,白底蓝字,十分雅致,似乎茶的香味儿正在其中飘出。“这是精准扶贫之后,浮梁县供电公司帮村里免费安装的。”说话的是磻溪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扶贫专干汪和根。他60岁,看上去十分乐呵。听说我来了解扶贫情况,非常热情地说了起来。虽然他的方言我不能全听懂,可慢慢也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我们这里扶贫,可是做了好事,做了高山茶产业。我们不叫采茶,叫‘采鲜草’。我原来在生产队做茶叶。我是1959年生的,印象最深的是用柴油机发电来揉茶。”站在新的村委会办公楼上,汪和根一指下面右前方,“就是在那个位置,以前大队的柴油发电机房就在那儿,一开起来到处都听得到。柴油机发电。那电可珍贵,不到点不开,到了点就关。一天也仅有晚上两三个小时可用。”
原来,秉承传统,这里的百姓可说是家家与茶有关,有种茶的、有制茶的、还有卖茶的。村里过去只做红茶,现在红茶绿茶都做。上世纪60、70年代,西湖乡政府在村里专门设立了茶叶收购点,村民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把“鲜草”卖给收购点。那时,村里仅有柴油机机房,用来进行菜籽加工、茶加工、稻子加工等,归大队(村委会)所有。每次村民们收了鲜草,全部称好,按一斤多少记上工分,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排队等着交上去。大队在第二天会抽4、5个人来做茶。
磻溪村山高林密,雨水充足,是天然的“鲜草”生长乐园。上等的“鲜草”每年长得令人喜爱。要保证“鲜草”的鲜,每次摘时,村民们那几天兴奋而劳累,根本无法睡好觉。红茶传统做法,是在太阳下萎凋,因为“鲜草”娇气,得当天采摘当天制作,最迟只能到第二天,否则就会变味儿。在“鲜草”成熟的日子,一大早人们便成群结队地上山,采摘下来,马上放到太阳下晒,晒了揉,揉了烘。每片叶子都得揉到、都得烘到,一步也不能放松,跟打仗似的,就为了在晚上能制出香味四溢的好茶。
从前是谷雨摘茶,红茶要经萎凋、揉捻、发酵、干燥4步骤,绿茶分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村里人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天上出太阳。可是谷雨谷雨,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雨与太阳交替出现的时候,偶有太阳,那真是特别珍贵。白天用竹篾来晒,“鲜草”晒老了不成,没晒好也不成,要保证摊晾充分,让叶片中的水分均匀散失,自然萎蔫凋谢,完全得靠人时刻守着。如若无太阳,便放入大队办公楼二楼的木板上阴干,不行还得用火桶来烘。
“采的‘鲜草’原来一芽2叶、3叶的都有,有的还大到了一尺长左右。可难揉呢。”据汪和根介绍,原来是用手揉捻,每片“鲜草”都得揉到,很精细的,偷不得懒。一斤“鲜草”得花一个半钟头,只能做三两干草。这还只是制茶的一部分。在绿茶烘干时,村民就在黄土房地上,开个小园灶,下面用炭盆子烧炭,上面围着竹篾笼,将茶放在笼上层来烘。要是绿茶杀青时,人是不能停的,头锅、二锅不停地炒。锅里温度高,人得弯着腰不停地干,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有时汗滴到锅里也不能擦。只怕绿茶炒不好,会成为花青。
“现在人们喜欢一芽1叶、2叶的,这种‘鲜草’现在更值钱。汪和根说起时制茶不断比划着,“我是边炒边出汗,没办法,只有我老婆在边上帮我打下扇子。”
说到电,据他说,村里是1988年通电的。当时埋电杆,要求达到1.1米深,他还去监管过。虽然只是昏黄的灯光,可也比没电好。随后没几年,听说有用电制茶的机器,便买来试用,“有电多舒服呢,比如,用电揉茶,人省事儿了,不累了。而一锅理条机可做5斤,只用1个钟头,出1斤半左右干草。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磻溪村现在改为了清明节前半个月采“鲜草”。虽然“清明时节雨纷纷”,可大伙儿也不怕了。因为用上了电,什么时候都能做茶了。而且,现在很少停电。村里的汪秀兰家是第一个申请用三相电的。“她是一个女人,也50多了,想到年纪大了,用电制茶当然更省力省心呢。”经历过用手揉“鲜草”的汪和根,现在还开着加工厂。因为用电可以揉、可以烘,可以烤……再也不用那么累了。仅2019年就加工干茶100多斤。
磻溪村虽然不是贫困村,却有47户贫困户。全村12个村小组,其中3个村上组在山上,贫困户有 6户。我们往那儿开去,开到村后,见一片古楠木群边,立着一座雕像,是个美丽而飘逸的采茶女,似与进村处巍巍的茶王雕像远远相呼应。一个村子有两座雕像实在罕见,真是显出与茶关系的深远和密切。
远远望见青林山时,我没有料到有这么多弯道。山路正好可以走一部汽车,行一短程转个弯,再行一短程又得转弯,山道弯弯难以计数。越行越上,待侧目向下看去,发现底下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谷,甚是惊险。约半个小时后到了山上,在一拐弯处,48岁的汪宪权穿着一件套头白色汗衫,一脸通红地等着我们。
“明天有大雨,这两天难得太晴,得抓紧时间。”他刚从茶园回来,这两天,他正在山顶茶园锄草。
青林山不算高,海拔约1000米。此前一直雨水不断,刚连续三天晴朗,村民都在自己的茶园里忙碌着。今年“鲜草”已采摘制作完毕,现在是锄草、松土、施肥的时候。汪宪权带着我们又前行了一会儿,到达了青林坑村小组。只见三面环山,村小组就像被抱在山中。临近山顶处依山几栋分散的黄泥做的土屋,立在山边,屋前有一些小块小块的菜地,几乎没有平地。汪宪权的厂就在左侧一个拐弯处稍平的地方,就像立于岩石之上。
厂房是铝合金墙体,进门处桌子上放着一张黄底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浮梁县首届‘复兴杯’茶王奖,10000元”。左边依次从小到大立着8台揉茶机,右边是三台大大的烘干机,正对大门的前面墙上有门,打开了,可见外面放着是一台煤气鼓风机。
大门右边还有一半厂房,走上两级台阶,里面是以前的黄泥土房子,用木板分为两层。里面放着长长的制茶用的理条机。那台鼓风机正是从外面送风至此理条机的。屋里两根木柱上挂着温度计,边上还有一台提香烘干机。
“以前这里是无田无路无电‘三无村’,2005年通的路。我小时候看到大人们在煤油灯下制茶,”汪宪权说,“看都看不清,还熏得难受。那时候可是费劲儿,采了‘鲜草’白天晚上地揉,还得在太阳下萎凋,产量很少。”原来山上没电时,他们利用山上的溪水买了发电机来发电,可是到了枯水期就不行了,灯也一闪一闪的。根本没想到过现在会用电制茶。
13岁就开始学制茶的江宪权,父亲是做茶叶包装的。“以前分得细,和做瓷一样,各环节都要人。”他看见大人们用手工揉茶,忙不过来还请人帮揉,而请人可比用电贵多了。到了1988年村小组通了电。这下电灯亮了,慢慢有了电视,用起了电扇等。等知道制茶也可以用电,有这样的机器时,他就想试试。
“我2008年装了三相电,买了揉茶机和理条机,就做起了加工茶叶。”因为用电,省时省力,山上这间原来的茶叶加工厂废弃了。在2012年,他租了下来。当时山上只有一台20千瓦的变压器。“后来不行了,最后就烧掉了。”随着厂子用电量增加,到了2014年供电公司来免费更换了一台120千瓦的变压器。随后生意越做越大,2017年厂子还进行了扩建,就是进门便看到的新厂房。
汪宪权特别爱笑,一开口就笑,“智能用电,省去了师傅眼力、手感、经验环节。绿茶设好温度完全可以去睡觉。” 看着厂里放满用电揉茶机,他又笑了,“这些都是慢慢增加、增大的。现在我厂里什么都用电,没电我什么也做不成了。”他笑着说。他后来又增加2个热风锅炉,还是以电带动,再用煤气燃烧送风。
站在厂门口,汪宪权指着山的另一边,说,“那边的扶贫茶园原计划3年后会有收成,村里现在帮贫困户流转了废弃茶园,提早了。他们还开垦了23亩新茶园,驻村第一书记余永菊这几天正带着贫困户在上面锄草、施肥呢。他们可真上心,为了提高茶叶质量,2019年一开年便请来了云南的制茶师傅,来帮助我们提高制茶质量。那师傅就是在我家里吃饭的,在我这里住了有两个多月呢。”
汪宪权2013年时,做茶还不到1000斤的,2019年达到了4000多斤。2019年5月,因红茶制作,汪宪权在首届浮梁“复兴杯”大赛获得茶王称号,虽为手工制茶,其中一些环节也用了电。
作为山村,磻溪平地少,高山多,林木葱郁,植被丰富。村里有300多户,1200多人口,半数青壮年在外打工,虽然不是贫困村,却有47户贫困户。为帮助他们精准脱贫,国网公司浮梁县供电分公司自2017年起先后派出了两位驻村第一书记。
望着终年云雾缭绕的高山,了解到磻溪村高山茶历史上的名气,驻村第一书记肖金铭心潮起伏,贫困户要致富、做产业,为什么不把山上的“鲜草”发展起来。除了做好一些短期、个性化的帮扶,他与村委村商议后,选定山上23亩土地,为贫困户发展高山有机茶园,并成立合作社,确定了走集体经济之路的扶贫方案。
后来,因工作需要,肖金铭不再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8年,浮梁县供电分公司又派出了余永菊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接下了他的工作。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余永菊同样对“鲜草”之事挂于心中。“浮梁茶”的牌子,历史悠久含金量高,要让它闪出光亮来。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面对茶园3年规划,站在青林山上时,余永菊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沉重。他每年年初制定精准扶贫工作方案,按照扶贫工作方案开展工作之时,将开展扶贫茶园工作放在重点。为让贫困户早日获利,还适时做了调整,帮贫困户先在山上流转了27废弃茶园。并定期请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从事锄草、施肥、补栽、采茶等工作。这样,在2019年清明节前后,新流转的一块茶园就收获了第一批“鲜草”。
看到通过立足本村实际,精准扶贫作产业,发扬传统优势,让“鲜草”化为致富宝,“村里贫困户特别感激,都把用‘鲜草’制出的茶称作‘扶贫茶’。“那些‘鲜草’就是在我这里用电加工制成的。”汪宪权乐呵呵地告诉我。在他的自动化茶叶加工厂里,因为实现了用电制茶,首批 “扶贫茶”制作起来也特别顺利。据他说,目前,整个西湖乡茶叶产量的90%是用制茶机器制作的,用电制茶户均数达到60%多。“村里全部通动力电,现在电阶也降了,用电更方便了。”
“供电公司还帮贫困户销‘扶贫茶’,当年就销售出去了400斤了。”汪宪权又热情地介绍道。村里当年底对贫困户进行了产业分红,按照劳动能力、贫困程度、脱贫年份,贫困户每户分到500-1300元不等的产业分红。今年村里那扶贫茶园又产出了上等的530斤“鲜草”,也全部制成了上等茶,销售一空。年底贫困户又可分红了。
第一书记余永菊2018年将磻溪村上报高标准台区改造。通过不懈努力,他所在的供电公司2019年投入60万余元对村子进行了高标准农网改造,增加3台变压器,家家通上动力电。现在,有能力制茶的贫困户都购买了制茶机器,他们在家就制作茶叶了。该村2018、2019年脱贫13户,39人。今年将有贫困户8户,12人全部脱贫。
精准扶贫,让山上的“鲜草”成为贫困户手中致富的宝中宝。村前村后的两座雕像,显示了村子扶贫的特色和做好高山茶产业的决心。此刻,阵阵风儿吹来,青林山上的树,发出了成片“哗哗”声响,真好像是拍着巴掌赞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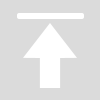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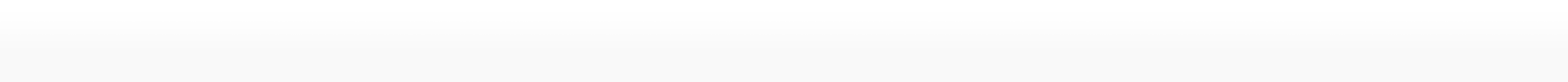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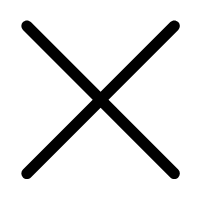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