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运朝向一个注定多义的人
[ 炙 ]
公元一五八二年。夏天像一卷被烤焦的菜叶,蔫蔫巴巴地覆盖着一个名叫明的王朝。空气中弥漫着深腐的气息,生灵窒息。
那是一个陷入高烧的王朝,体内的火苗与体外的光焰,隔着薄薄的皮肤、骨骼,热切地呼应。如果闭上眼睛,凝神去听,听得清他急促的呼吸吐纳声,间杂喘啸之音。恍如微小的箭矢,一支一支,疾速擦过滚烫的空气。
此时,一团冰冷,正在明的体内缓慢位移。那不合时宜的冰冷,携带舒畅,也携带刺痛,一寸一寸碾过明的腹心。那是一支绵延十余里的队伍,由七百余首尾相接的车马、三千多军卒役夫,以及一尊巨大敦实的棺椁组成。它从明王朝古旧版图的红心处出发,一路向南,向南,朝着一个名叫江陵的地方挺进。所过之处,沸尘蔽日。
京城、江陵,一庞大一瘦小,一繁华一荒僻,一荣尊一寂寞。之间的距离,用车马的轮辙来丈量,约等于二十个日日夜夜。
公元一五七八年,沿着同样的路线,上演过极其相似的一幕。空间的迁移,远比时间和生命来得缓慢。路边的风景来不及改变,奢华起伏的大轿已换作了端肃平坦的棺椁。轿里端坐的人,从此躺倒下来,笔直地,冰冷地,与道路平行向前。
从公元二零零六年春天的深处望去,那团冰冷,最初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一处馆舍生成。那一方位,与五百多年后的湖广会馆,大致重合。公元一五八二年的春天,在馆舍深处的一张床榻上,俯卧着一个形销骨支、白须皓首的老人,疼痛正在他的身体中肆虐。他的手,握住一管饱含墨汁的笔,颤颤巍巍落在奏折上。奏折从紫禁城一路奔跑而来,墨迹未及干透,又匆匆奔跑回御案前。在一叠叠奏折中间,夹杂着老人的奏折。不同的文字,表达着同一心愿——乞归生地。
从生地到葬地,在这个平朴简洁的短语里,涵盖了每个生命或短或长的一生。老人希望两者,在他的意愿中、他的呼吸间重合。
哪怕生前领受过无上的荣宠,却注定无法如愿圆满自己的一生。那是一个匍匐在地的臣子的命运,老人的命运。臣子是另一意义上的奴仆,另一意义上的祭品,哪怕清刚自负,傲慢骄奢,雷厉风行,刚愎自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可以修改法度,掌判生死,宣讲道德,纵横疆场,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生前,在死后。
最终,棺椁一路南行,栽入大地。过程隆重、鲜灿。拂去百年尘埃,在沿途匍匐垂泪的人群中,会否有一个人,预见到两年后华丽的棺椁骨架散落、碎砾铺地的一刻。命运那雍容华美的包装,将假借一个人,一双手,一种意志,还原它残酷的面貌与本质。
冰冷与炙热的对抗,继续在明的体内进行。直至公元一六二八年,努尔哈赤的铁骑碾碎明早已羸弱不堪的躯体,挣扎结束。
高热之后的大地,冰寒一片。
[ 史载:明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殁于京师。神宗赐搭建丧棚的孝布五百疋,大米两百担,与母弟、宗室璐王合赠银二千三百两、香油一千斤、香烛一千对、薪柴一万斤……朝廷特许京城设祭坛九座,因赴吊者太多,后加设七座;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派四品堂官与锦衣卫护送其灵柩返回故乡江陵,送葬队伍绵延十余里。]
[ 链 ]
那一命定的时刻,他早已预见。
预见,却无力阻挡。
那个躺进棺椁的人,再没有早朝、经筵、奏折和繁缛仪式来干扰他的宁静,也再没有明枪暗箭可以洞穿他归于透明的心魂。但绵延的生命链,不会随着一个生命的谢世,戛然断绝。他的子、他的孙,他的亲、他的爱,他的仇、他的恨,还在时光中接续。如同命运,不只在脆弱的肉体上寄生。
集权时代,生命如一芥蓬草,来自御座的一声叹息,便足以将之连根摧折。
那叹息出自一个人的胸腔。除了身上的服饰有着特定的象征意蕴,他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五官四肢和嘭嘭跳动的心脏。起卧之间,飘忽无定的思维在他的大脑里奔窜,郁闷喜悦苦恼忧伤愤怒无助怨忿失意恐惧纠缠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可再微弱的叹息,一旦出自他的胸臆,便像紫禁城屋宇檐角盘踞的兽、大殿天宇正中回旋的花,从具体的形上升为抽象的意。这叹息,携带着自历史深处积聚的万钧之力,披盖四野,可以在瞬间将一切倾坼。
公元一五八四年,叹息从一个名号万历的年轻皇帝口中吁出。一团带着火焰的力,疾速穿过明王朝腐滞的空气,似一只暴虐的铁拳砸在了一个叫江陵的地方。
一个名字戴上了诅咒。无形的锁链,赠予死去的魂灵。有形的锁链,环套在他的子他的孙的脖颈上。他的亲他的爱,碎作齑粉。黑色的血在汩汩的地层间奔淌,猩红的泪在娇嫩老朽的面颊上奔窜。
锋利,无可抵挡。乖谬,无可抵挡。暴戾,无可抵挡。毁灭,无可抵挡。
无常的命运,无人可以阻挡。
从此,墓园荒芜。
[ 史载:明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四月,神宗下诏查抄荆州张府。司礼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木舜急赴江陵。途中即传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后老弱妇孺饿死十余人。张居正之子懋修不堪忍受折磨,自杀未遂;敬修羞愤难当,自尽身亡,临终写下一纸绝命书。张家阖府男丁“俱令烟瘴之地充军”。]
[ 罪 ]
一个动作重复千万次就成为仪式。一种程序绵延数千年就成为习俗。一句话被不同的嘴陈述上百次,就可能成为他人耳朵里的真实。尽管,这真实万分可疑。
耳朵,是骨质绵软的器官。稍稍比心坚强。
公元一五八四年,二十一岁的万历坐在紫禁城的深处,沉思。无数臣子的声音,在他耳边聒噪。那些话语指向一个人,一个曾在御案前匍匐、并辅弼他十年的人。心目中原本清廉刚正、事事正确的形象,正在无数的声音中变形,滑坠,荒芜,破碎。无数的往事,匆匆复活,哪些茂生,哪些凋敝,哪些指向相互悖离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
最终,年轻的皇帝将用一个无情的手势,掀开远方的一尊棺椁,褫夺他曾嘉覆在一个臣子身上的所有荣耀。那些荣耀以名衔、金银、坐蟒、墨宝、恩赐的祖先诰命、缓解腹痛的一碗椒汤面的形态,在十年的时光中陆续颁发。而褫夺,只需要一个瞬间、一道圣旨、一个简单的手势,只需要将心变得比耳朵坚强,比石头坚硬,比时光更无情。
年轻皇帝在假想的果决的动作中,注入了什么样的期待,已经不再重要。他的命运已定,明的命运已定。五百多年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
罪,是行动的借口,是可以放在台面上的武器,是暗含复仇的旨意可以毁灭活人、也可以戳戮死尸的堂皇工具,是互为阵营的文官集团为欲望、利益而战的道德铠甲,是一人独享的御座前、争先恐后的匍匐者为历史化妆的油彩。
公元一五八四年,它瞄准了一个名叫张居正的人。如网,笼罩。
经过时间耐心的洗刷,每一段历史,都不复有本真的气味。他是永远的婴儿,意义不明地哭泣、发笑、咿咿呀呀,惹得后世者心疼又发愁,需要用想象不停地去喂哺。
偶尔,他抛出一些线头。诸如十二岁的秀才、十五岁的举人、二十二岁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裕王府讲官、礼部尚书、内阁首辅,这些线头掩埋在灰尘呛鼻的故纸堆里,从《明神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万历野获编》,和一本本敦厚的地方史志的字里行间飘浮而起,构成一级级阶梯,叠加至一幅泛黄的画像前。那是后人,如我可以梳理、组合、回归、延伸的路径——文字的路径——通向的,是否我所寻找的那个人,历史不会作答。
不同笔下斟酌的文字,勾勒出不同版本的同一个人。只有那些不会狡辩的年份,让时间成为一枚枚钉针,钉住一个人基本的命运轮廓。还有一个年轻皇帝用朱笔御批的——罪,刺目地悬挂在历史册页上。那是用文字打造的中式十字架,也称耻辱柱。
[ 史载:明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张居正去世仅半年,一应封号被褫夺。万历十二年,其罪状被定为“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
张居正死后三十年,万历依然在位、朝廷未予平反之时,江陵县令石应嵩募资重修张之墓地,并在《张文忠公改葬碑文》中写到:“功既震而身危,狡兔良弓已矣;事盖久而论定,云台麟阁依然。” ]
[ 恨 ]
世间的恨,总可以找到理由。不管这理由,隐藏得有多深,延伸得有多远,曲折得有多荒谬。
公元一五八四年,端坐在御座上的万历,从胸腔吁出那口压抑多年的叹息时,内心怀有的复杂情愫已混沌在时光深处。倘若那是虬结一团的线,也许有一根是快意,有一根是豪气,有一根是舒畅,有一根是胆怯,有一根是愤怒,有一根是懊恼……拂开这一切,必有一根线头,清晰可辨,不可缺少——那就是仇恨。
心中无恨,不会向一个多年爱惜如父的人,掷出致命的一笔朱批。心中无恨,不会忍心将一个忠顺臣子毕生的光荣,尽数删除。心中无恨,不会让一位师尊的十年心血泼洒在烈日之下、冰寒之上,曝晒既而冷冻。心中无恨,不会将自己过往的种种感恩之举、信赖之心视作愚蠢,一概抹杀。心中无恨,不会忍心将一个无辜家族的命脉乱刀砍剁。
对于一个曾尊为师视作父、倚重过依靠过的臣子,他恨的,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看得见,一个年轻皇帝内心的坍塌。他的坍塌,发生在层层宫墙、重重帷幕的背后,发生在无数次不曾出口的无声呐喊中,发生在九岁登基端坐于御座之上的阵阵颤栗中,发生在严厉的母训和群臣乐此不疲的劝谏声中,发生在不断堆积膨胀的集权制度那庞大无比的阴影深处……
他,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之上。站在最远的臣子,也许连他的眉眼都看不真切。
没有人看得见他心脏骤停的瞬间,没有人感受到他呼吸不畅的痛苦,没有人允许他像风一样自由地奔跑。他,可以嫔妃如云,可以傲视天下,可以号令四方,可以尽享珍奇珠宝、美味珍馐,却没有恣性的权力。
从登上御阶、穿上龙袍那天起,他便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绵延数千年体制上的一个链环。如同冠服上隆重、华美的纹饰,不可随意更改。哪怕冕上的珠坠,不断地阻断视线,却无法伸手拂开。哪怕累赘的装束,不断牵绊他的脚步,也不能断然删减。一种命运选择了他,而他无法选择命运。
也许,他仇恨的,仅仅是一种命运。这命运在公元一五七二年猝然降临时,九岁的他还在懵懂之中,他的手被送到一双陌生的大手中。那手,清瘦刚硬,但温暖。让他在瞬间惊醒。惊醒,既而惊慌。
那双手,牵着他走过了十年。慢慢地,那双手成为他意志的一部分,长进了他的掌纹、他的身体、他的灵魂。无论他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他都无法轻易离开那双手。他被引领着,无权选择自己甘愿的方向,趔趄向前,向前,直到公元一五八二年,那双手断然松开。
片刻的怔忡之后,是怀疑;片刻的怀疑之后,是惊喜;片刻的惊喜之后,是狂放。
也许,这位年轻的皇帝,将一双手的断开,错觉为一种命运的撤离。为了让它消失得更彻底,他要让与那双手有关的记忆,摆脱十年时光积淀的尊崇定式,他要将那双手的主人,曾与他发生过的所有关联、所有因果、所有爱恨,一刀斩断。
无情,残忍,决绝。
公元二零零六年春天,一个并不聪慧的女子望向历史深处,如此猜想。
[ 史载:明隆庆六年,张居正以顾命大臣之隆望辅弼幼主。时,万历帝刚满九岁。主政十年间,张居正以清峻谨严的风格,推行其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的政治主张。
明万历元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府库空虚,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超出三分之一;至万历十年,“岁入白银达四百万两,太仓积粟可支数年”,“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粮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
[ 因 ]
事事皆因,循环为果。当乖谬的命运朝向一个人,死后的悲惨与生前的荣耀,构成一对因果,与巨大的反讽。
服侍明王朝三十五载,意味着匍匐在地三十五个春秋、上万个晨昏。之间,每一个年份的历史都不寂寞。公元一五八二年向后,五百年间,每一年份的历史同样不曾寂寞。寂寞的,是一个被深埋地下的臣子。
他,属于明。明的历史已告终结,他的命运还在跌宕绵延。五百年间,围绕他的历史功过、谋事做人,贬损者众,赞誉者众。
历史从来像一个布满镜子的迷宫,真实的、虚假的在之中交相辉映,互为迷惑。走进去,歧路丛生,没有一条路可以抵达最终、也是最初的真实。
辅弼年轻皇帝的十年,一个臣子阅过的奏折、写下的信牍、做过的决断、表达的忠诚、投入的心血、说过的谎言、违背的意愿,已成为历史无法看清辨真的部分。稍稍可以辨识的,是由瘪而盈的国库,是四野边地的安定,是政令在驿道上飞速奔驰的叠影。一个人的功与过,从来难以分明边界,何况五百年时光的涂抹和历史刻意的暧昧。
他,成为史册上一个多义的词组。
从有限的史册中跋涉出来,掸掉身上的灰尘,在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明、一个万历帝、一个居正公。
公元一九六六年,两个同样来自明王朝的君、臣,命运再次悲剧性地重合。一个在北京,被掘墓毁尸。一个在荆州,被开棺散骨。执拗的命运,不可阻挡。
尽管世间的任何评定,再无法抵达一个死者的耳边,但可以让活着的子孙,在拜谒的时刻,或歌或泣,或悲或欣。
公元二零零五年春,一座崭新的墓园出现在一座名为荆州的古城。那一方位,与五百年前的江陵大致重合。
墓园离我工作的地方不到五百米,步行大约五分钟。常常,在夜半回家的路上,乘车经过墓园。墓园前的街道空无一人,一盏路灯静静标示着墓园的方位。我侧过头去,看墓园在窗外无声滑过,红墙乌瓦、门前的一对石狮,依稀可辨。
那里,曾是荒凉数百年的一带乡野。遇雨天,泥泞不堪。翻修前,豪华的棺椁,经过几毁几誉,已削减为一个狭小的青花坛和一方朴素的石碑。生前硬朗清刚的骨骼,只剩几根残骨,历历可数。数不真的,是一个注定多义者的命运之果。
那果,还没有瓜熟蒂落,还在继续生长。在数不清的生命早已被历史彻底掩埋之后。如同墓园,会苍老,会焕然一新,还会再度苍老……
那个注定多义的人,他的子他的孙,一代一代朴素地生活。他们从烟瘴之地陆续返回故乡,散居在墓园的周围,五百年间,他们仿佛一个忠诚的怀抱,将这位让他们荣耀也哭泣过的先祖,紧紧地团在怀中。也有的,散居海外。每年,总有一些时刻,他们会向着地球上的这个方位,遥遥祭拜。
关于这位先祖,何为因、何为果,何为荣、何为辱,何为爱、何为恨,对于默默生息的他们,已经不再重要。
属于历史的荣辱,还给历史;属于生活的,归于朴素的生活。
[ 史载:明天启二年,朝廷追思张居正的大功,复原官,予祭葬,张家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居正讼冤,交给部议后,给还张居正后人官荫和诰命。张家子孙陆续返回江陵(现属湖北省荆州市)。
公元一九六六年,已成荒坟的张居正墓遭红卫兵破坏。棺木被打开,尸骨散落。张家后人于夜间悄悄拾得几根残骨,装入一青花坛中,掩埋。公元二零零五年初,修葺一新的张居正墓园,在荆州正式竣工。那里曾是年近三十岁的张居正返乡闲居六年,所筑“乐志园”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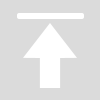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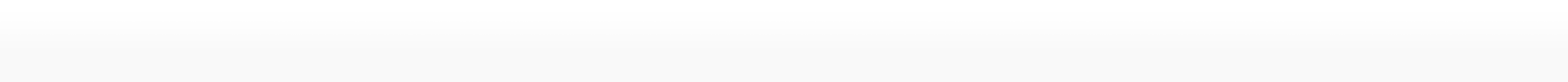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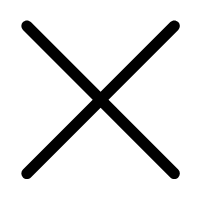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