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昭君无关的祭奠
[ 墨痣 ]
一颗痣,覆盖一个人的一生。它的颜色,必是浓墨的黑。
这颗痣,在虚无中生成。它自画工灰暗的意念凝聚,沿他手中的笔端滴落,落在命运的画布上,洇开,便有了黑的残酷,黑的霸道,黑吞噬一切的魔力。
这颗黑痣,将隐蔽的诅咒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它模糊了一个女人的容颜,遮覆了一个女人的风姿,湮没了一个女人内心亮色的渴念,和关于未来的众多可能。它让深宫的寂寞更加绵长,镜中的影像愈加飘忽,让时间成为布满无数缝隙的纱网,黑轻易渗入,充填,膨胀,凝固,与时间化作一体,成为推不开躲不掉的宿命。
隔着两千年的时光,我遥望汉宫深苑中的那个女人。目光越过一道道宫墙,在谜阵般铺排的楼阁亭榭间搜寻。满目裙裾飘飞,满耳环佩丁当,谁是那个独独不肯迁就画工内心阴暗的女人?唯一线索——她,名嫱。
时光神奇,曾经模糊的慢慢清晰,曾经清晰的渐渐模糊。
名嫱的女人站在一扇窗前。她的面容似水中的倒影,波漾不明,我却看清,一根根青葱的藤蔓正在她心间生长,缓慢缠绕。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爱恋,由无数汉宫女人的内心出发,指向唯一的君王,皇座上的男人。嫱不知,几年后,她的心会被这没有路径抵达的爱恋,裹缚成一枚茧,无法通畅地呼吸。
另一处宫殿,正在阳光下抖落壮硕的暗影。君王的案几上摆着一幅画。一颗硕大的黑痣端卧画中女人的面颊,突兀,诡秘,阴险。画工的阴谋,将经由君王的一个手势,得逞。轻轻一拂,名嫱的女人就被送上命定之途,再无悬念。
没有人知道,汉宫深苑中,有多少女人的心成茧。她们最终沉溺于时光的渊深处,无迹可觅。而嫱,浮上历史册页,她找到了突围深宫的方式——嫁。剥掉心上层层裹缚的藤蔓,在君王的御座前,嫁给异域的王。
让初相见,成为永相诀。那是汉宫女人——嫱独特而决绝的爱恋方式。
这爱恋混沌不明。从头至尾,一颗墨色的痣将之无情覆盖。
[《乐府古题要解》载:“王嫱字昭君,汉元帝时,匈奴入朝,诏以嫱配之,号胡阏氏。一说汉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案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传说,画工丑其形,点了一颗硕大的落泪痣。这颗痣,改写了这个女人的命运。 ]
[ 琵琶 ]
在许多乐器的身体中,找得到一棵树的魂魄。琵琶如茎,精血充沛,刚健有力,有累世风雨也弹拨不断的结实与铿锵。纤指急弦,狂风骤雨,仍稳伫如故,不输金石。
公元前三十三年,琵琶抱在嫱的怀中,嫱斜骑在马上。
绵延的马队离长安,出潼关,渡黄河,过雁门,一路向北。马后桃花马前雪。嫁给异域的王,便是嫁给了大漠风沙、荒原孤寂。那是比汉宫深苑辽阔数百倍的寂寞,同样难以跨越。琵琶是唯一跟随的解语之物。
草莽的族群,陌生的语言,粗砺的生活方式,如风沙扑面,磨砺出隐约的疼痛。嫱,这个女人,在撼动帐篷的呼呼风声中,可曾后悔过当初的决绝之举,可曾落下点点滴滴思乡的泪。落下了,也将迅疾融化在沙中、土中、风中。
与辽阔荒漠相匹配的乐器,有胡笳、羌笛,细悠如诉,似风游弋。公元前三十三年冬天,塞外,琵琶的铿锵之音加盟进来。它从汉族女人嫱的指间汩汩而出,在茂密的草叶尖上流淌。那是诉说,也是倾听。
天地之大,唯有琵琶听得到懂嫱内心的声音,唯有嫱听得真琵琶的每一声悸动。
锁闭深宫数年,嫱沉淀入骨的怨尤,在琵琶声中泄露。御座前毅然请嫁的一刻,嫱内心翻涌的潮汐,在琵琶声中回响。远望长安不见,嫱无处诉说的乡愁,在琵琶声中喧腾。
“光明汉宫”不过一瞬的华灿,换得的是漠漠无边的寂痛。嫱,成为林立干戈间一袭灿红的丝带,两个民族间抽象的和解符号。因了她,数十年间,边地战事偃息,干戈之声不闻。
即便如此,荣宠加身的嫱也难弹出欢悦之音吧。她请归的声音,一再被回绝。最终,一掊香魂归于大漠。
塞外,琵琶音绝。
[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自昭君和亲后,北方边陲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 ]
[ 桃花鱼 ]
鱼,悠游在名为香溪的河中。河,躺在名为秭归的土地上。
明明是鱼,却借来了桃花的名字与身形。桃花鱼,是游动的点点桃花,在每年三月如期而至,赋予香溪水七彩的妩媚和俏皮的灵动。
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种忠贞的鱼。与来自香溪岸边的嫱,有着同样美丽的姿容、纯真的心地和执拗的性情。
传说,嫱远赴北漠前,被君王恩准回乡省亲。她乘坐龙船泛舟香溪,琵琶声声如泣,惊落片片桃花瓣。泪遇其上,化作尾尾灵动的鱼儿。船工随手摸起一条小鱼,嫱深情唤之——桃花鱼。
源于民间的传说,是温度适中的心愿。即使逾越常理,也温暖动人、浪漫可心。
我更愿意想象,公元前三十六年,十六岁的嫱坐上雕花龙凤官船,顺香溪入长江,逆汉水越秦岭,被送进汉宫深苑时,桃花鱼一路隐秘相随。它在长安相对干燥的空气里用力地呼吸,在嫱辗转不安的睡梦中游弋。它浑身散发出的来自家乡的气息,渐渐让嫱安静下来进入酣眠。
公元前三十三年,桃花鱼再次经由神秘的通道,陪伴嫱来到塞外。它在嫱的琵琶吟诉中游动,在嫱滴落沙土的眼泪中游动,在嫱举头翘望的目光中游动。
在不为人知的神秘通道,桃花鱼畅游无阻,来去自如。它在梦中带给嫱长安的讯息,家乡的讯息,也带回嫱无处落定的思念。
两千年来,桃花鱼潜流于时光深处,一直游进公元二零零七年的香溪,游进我的想象。伸出手,触碰它美丽沁凉的身体,能否感受到嫱——那个美丽汉代女子的些许讯息?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昭君字嫱,南郡(今湖北省秭归)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 青冢 ]
匈奴,一个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当一个汉族女人敏感纤柔的神经,与之触碰,能否激发出风荡草原般壮阔的爱恋?历史不肯作答。
在删繁就简的历史记载中,嫱,嫁两夫,生三子,历经三代单于,在第三次被迫嫁时辞世。一个女子柔细的内心筋脉被忽略不计,她隐秘的情感诉求被删除干净。
那是成为一个符号的代价。
史载,有汉一朝,充当两个民族间和解符号的女子,十又有三,多为公主。她们在人地两生的异域忍受了多少屈辱、悲辛,又享受过多少欢畅、荣宠,无人明了。年复一年,风沙憔悴着她们的容颜,羊膻改变着她们的气息,严寒冷却着她们的指温,住穹庐被旃裘的生活改写着她们的习性,而她们内心的牵念与曾经的爱恋,在寒天漠地间曝晒。那是陪伴在异域王身边的她们,无力呵护的。
时隔两千年,纷繁朝代更迭而逝,嫱的名字,在史册上存留下来,在民间记忆中延续下来,在无数诗文中烙印下来。有人感叹,有人赞颂,有人悲怜。
从一个符号回归一个女人,普通的、血肉充盈的女人,如此一段人生,不幸还是荣耀?二零零七年五月提前到来的暑热,蒸烤着这个小小的问句。
答案,早已终结。
两千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名叫嫱的女子躺进一处坟冢,正解一并被埋入。两千年间的众说纷纭,不过向着那方青冢的遥祭。
与汉代女人嫱的命运,统统无关。
[ 史料载:昭君死后葬在大黑河岸畔(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塞北纪游》:“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家。”“青家”墓碑上刻有: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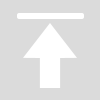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3 版权所有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 邮编: 330046 电话:0791-83986935
赣ICP备2023004682号-1 技术支持:南昌广电全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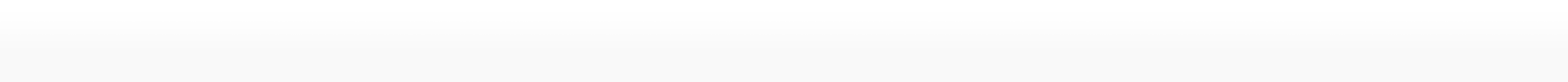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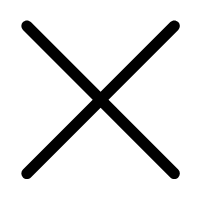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
赣公网安备 36010802000875号